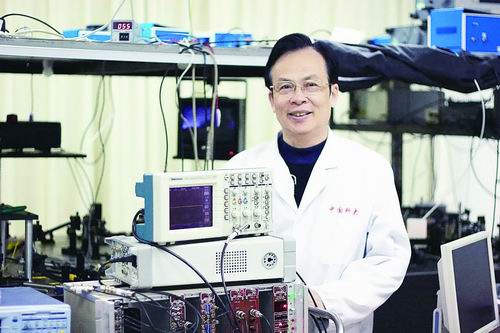
郭光灿在实验室。受访者供图

1983年6月,在罗切斯特大学参加国际量子光学会议的中国人合影(左一为郭光灿、左二为邓质方、右三为彭堃墀、右四为吴令安)。 吴令安供图

郭光灿(左一)听取课题组学生报告。受访者供图
“统统都是假的!完全是商业炒作!大家不要上当!”为辟谣所谓的“量子产品”,郭光灿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在科普演讲中这样澄清了。
近些年,量子科技太“火”了。最火那阵儿,市场上冒出各种奇怪的东西——量子水、量子鞋垫、量子眼镜、量子速读、量子医学……仿佛“一切皆可量子”。
如此啼笑皆非的现象,总让这位81岁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恍若隔世——中国量子科学曾经有多冷,他是有切身感受的。
上世纪80年代到2000年这20年,是中国量子学科发展的“冰期”。那时,郭光灿先后投身量子光学和量子信息研究,是妥妥的学术圈“少数派”。懂量子的人实在太少了,申请研究经费经常碰壁;而每个铩羽而归的夜晚,郭光灿连个倾诉和商量的人都没有。
但郭光灿觉得量子研究太重要了,也坚信“国家早晚会大力发展”。因此,尽管一连18年苦坐“冷板凳”,他也从没打过退堂鼓。
1 罗切斯特的约定
郭光灿迄今的人生刚好可以分成两段,41岁前和41岁后——命运的齿轮,在他41岁那年开始转动。
1983年,郭光灿41岁。这一年,他参加了在美国罗切斯特大学召开的第五届国际量子光学会议。
一切都像是命运女神的安排。原本做激光器件研究的他,在1981年出国留学加拿大之前,和量子光学结了缘。他摸索出一条理论研究的新路——因为“没钱搞实验”,他想到用量子力学去研究光学。但彼时国内由于经典和半经典激光的理论研究已经相对完备,他转做量子光学,听到的几乎都是反对声和质疑声。
尽管如此,他对量子光学的好奇心反而更强了:“这其中的奥妙,我就是想要弄清楚!”
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留学期间,郭光灿才发现,在国内不被认可的量子光学研究已经落后国外20年了。
第五届国际量子光学会议只有8个中国人参加。除郭光灿之外,还有当时正在罗切斯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邓质方、在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进修的彭堃墀和谢常德夫妇以及在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物理系读博的吴令安等。
同在异乡为异客。联想到国内量子光学研究的落后,大家分外感慨。
当晚,邓质方邀请他们到家中叙谈。赶上妻子不在家,家里冰箱里有什么,邓质方就招待什么。大家切西瓜做果盘、拿冰激凌当甜点,边吃边聊,直到凌晨两点。
畅聊的主题只有一个:国内量子光学研究无人问津,跟国外热闹景象反差太大。8个年轻人意气风发,决心回国之后共同推进中国量子光学学科的发展,并约定谁先回国谁就先组织队伍。
两个月后,郭光灿成为8人中第一个回国的人。
2 “寄生”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量子光学学术会议
回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简称中国科大)的郭光灿感到使命在肩,第二年,他就想通过举办学术会议的方式扩大影响。但是,要办会,首先要有组织会议的资质,还要有钱、有人。
他一个副教授,只有一腔热情。
郭光灿在激光圈里还是有人脉的。他听说,中国光学学会激光专业委员会要在安徽滁州开会。机会来了!
他找到激光专业委员会主任邓锡铭说:“我们想开一个量子光学会议,但没资质,能不能‘寄生’在你们的会议中间,开一个‘小会’? ”
邓锡铭勉强同意:“会可以开,但我没有多余的经费给你。”
郭光灿又找到时任中国科大教务长尹鸿钧。这次郭光灿运气不错,物理专业出身的尹鸿钧十分支持他,特批2000元会议费。
会议总算可以开了,但邀请谁参会呢?当时国内几乎没人研究量子光学。
郭光灿干脆广发“英雄帖”:只要感兴趣,都可以来!
还真吸引了一批人,也有一些参加激光会议的人抱着好奇心留了下来。那天,他特意数了数,参会人数居然超过半百——尽管大多是来瞧新鲜的。
“总算有人知道量子光学了。”郭光灿挺满意。
这个会议自1984年起被延续下来。也是从那年开始,郭光灿开始在研究生课程中开设“量子光学”,并自己动手编撰教材。所谓教材,不过是几十页油印的讲义。
有了教材,郭光灿便开始抓住一切时机讲课、作报告,让“量子光学好不容易燃起的火苗不致熄灭”。慢慢地,对量子光学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
这期间,“罗切斯特约定”的其他人也陆续回国。彭堃墀、谢常德夫妇回国后得到山西省的重视,在山西大学建立了国内第一个量子光学实验平台,后来又建立了国内第一个量子光学重点实验室。吴令安回国后加入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从事压缩态和量子密码的实验研究。
3 “绝不能让历史重演”
1988、1989年,郭光灿接连获得教授职称、成为博士生导师。
如果郭光灿安于在学校教书、上课,做点理论研究,教授头衔足够他这个在渔村长大、不善交际的人安稳过完一生。
但人生没有如果,他的性格、眼光和视野,决定了他“无福消受”这种人生。
20世纪90年代初,作为一个已相对完善的基础学科,量子光学的理论研究已经不能满足郭光灿了。他不断想,量子光学下一步该往哪儿走?
一次阅读文献,“量子信息”一词让他眼前一亮。
这是个国际学术界刚提出不久的研究领域,研究者并不多,是彻头彻尾的冷门领域。但郭光灿的直觉告诉他:这是一个非常有竞争力的领域,恐怕会对国家未来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值得“大搞”。
量子密码、量子测量、量子通信乃至量子计算机,都是量子信息的范畴。他想,如果其他国家搞成了,中国没跟上,将会是灾难性的。想到量子光学的落后,郭光灿下定决心转攻量子信息学:绝不能让历史重演!
可他和团队连“经典信息”都不清楚,谈何“量子信息”?从头开始啃!他请来中国科大信息学院教授朱世康——比他低一级、来自无线电电子学系的师弟,给团队开“信息论补习班”,从“0101”开始讲解编码等信息理论。
郭光灿不仅上课仔细听讲、认真做笔记,下课后还追着朱世康问东问西。因为实在没法儿一下子全搞懂,他就让朱世康给团队留下一本教材,团队每人研读一章,然后再集中讨论。
这本教材整个团队“啃”了3个多月。功夫不负有心人,结合“量子”和“信息”,他们很快找到题目——量子编码。
4 “没钱?那就去找”
郭光灿把这个题目布置给了段路明——这是他在讲授本科光学课上发掘的苗子,收在自己课题组读研。段路明在202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一开始,量子编码感觉已经被前人做“到头儿”了,段路明有点士气不振。
但郭光灿不这样看:“这个领域才刚刚开始,遍地是黄金,仔细找,肯定能找到。”
当时所做的编码,其量子比特是独立的消相干。“我们来一个集体消相干会怎样?”
还真做出了名堂。“集体消相干”更省事:他们把不会消相干的特殊量子态称为“无消相干子空间”,只在需要的时候再把会消相干的量子编码到这个态上,以避免出错,称之为“量子避错编码”。“量子避错编码”成为世界上3种不同编码原理之一。
1997年,郭光灿和段路明把这一成果发表在《物理评论快报》(PRL)上,这是中国科学家最早在量子信息领域的显著成果。论文发表后让一些“老外”很惊诧:中国人居然也能有这样的进展。
一次,郭光灿在组会上分享最近的前沿动态时,介绍了量子克隆。
一个量子信息不能克隆出两个一模一样的量子信息,叫作量子不可克隆。克隆不成功也可以,一个克隆成两个,跟原来的相似程度叫保真度。保真度小于1,就不一样;保真度等于1,就完全一样。
“我们就提出一个新的克隆原理。克隆机成功克隆一个信息,留下来;不成功的丢掉,成功的最大效率是多少?”
段路明和郭光灿算出来了这个极限,并命名为“段-郭界限”。这个界限不可逾越,否则违背量子力学,被称为“段-郭界限不可逾越”。
这是他们发表在PRL的第二篇高水平文章。“量子概率克隆”的一位审稿人惊讶于郭光灿研究组的犀利,感慨道:“我们怎么就没想到?”
此时,郭光灿在领域内已经小有名气。在美国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郡分校担任物理系终身教授的中国学者史砚华,在一次量子信息的学术会议上几次被国际同行追着问:你认不认得G.C. Guo?
史砚华后来见到郭光灿时跟他说:“这真让人骄傲。”郭光灿倒很淡然:“中国人是能够超过他们的。”
尽管郭光灿研究组在国际量子信息领域逐渐崭露头角,但毕竟圈子太小、影响力有限,在国内也很难引发关注和重视。他想赶紧做出一些“动静大一些”的成果来,好让人们“尽快见识量子信息的厉害”。
这期间,郭光灿研究组还只是在理论层面“查漏补缺”,要做出更重要、更领先的成果,还得捡起实验研究这个法宝。
做实验要仪器、设备、耗材,说白了必须得有钱。当年郭光灿就是苦于缺钱才转身做理论研究的,现在的他依旧是个“穷光蛋”。但是,这一次他知道,不能继续躺在理论研究的舒适区。
“没钱?那就去找。”
5 “一个人在无尽的祈愿里承受风雨”
话虽豪气,但转攻实验研究需要的经费,跟他做量子理论研究时四处“化缘”拿到的,完全不是一个量级。
课题组那时能申请到的经费非常有限,无外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几万元,结题后还要隔一年才能再申请。
而郭光灿“找钱”还面临一个现实难题。量子相关研究过于超前,国内对“量子信息”的争议很大,很多人对诸如“薛定谔的猫”“量子的叠加态纠缠态”等概念不理解,觉得“不靠谱”,甚至认为是“伪科学”。
面对质疑,郭光灿嘴上忙着解释,心里也跟着着急:这个领域方兴未艾,眼见国外相关研究越来越红火,国内这样下去可不行。
因此,当1997年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基础研究重大项目计划——973计划被提出时,郭光灿立刻觉得机会又来了。
入选的项目不仅能拿到“大手笔”的资助,更代表着国家支持的方向。
“‘973’就是为量子信息这样前沿、重要的研究而设的!”说干就干,郭光灿立即填表申报。他像小学生做作业一样认真准备,一笔一画绘制着心中中国量子信息学大厦的草图。那些日子,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憧憬,整个人都乐呵呵的。
然而,连续3年,他乘兴而来、铩羽而归——
第一年,申报表提交之后石沉大海;第二年、第三年,他获得了第一轮答辩的机会。但关于答辩的场景,他的记忆已经模糊,只记得他一个人背着厚厚的电脑去汇报,到处碰壁。郭光灿苦笑着回忆说:“我在台上讲半天,人家还是投来怀疑的眼光。”
郭光灿不肯放弃任何可能的机会。
他清楚地记得,1998年的大年二十九,他应中国科学院院士郑厚植之约,从合肥赶赴北京开研讨会。从事低维量子结构物理研究的郑厚植听说他也在申报量子方面的“973”项目,想看看几队人马能不能“合兵一处”,提高申报成功率。
待到开完会要返回时,郭光灿才发现已经买不到回家的车票了。更惨的是,招待所的服务员都回家过年了,饭都没的吃。那应该是他在为量子信息“化缘”经历中最狼狈的一次:春节期间的北京城,家家户户张灯结彩、鞭炮阵阵,但郭光灿听得最清楚的是肚子饿的“咕咕”声。
郭光灿是一个过惯了苦日子的人。3岁时父亲被日本人抓去做壮丁客死他乡,不向生活低头的母亲,把他和两个哥哥拉扯大,坚持送他们去上学。邻居挖苦她:“饭都吃不饱,还让孩子读那么多书,是想当大官吗?”
在这样的条件下长大,郭光灿什么苦都吃得下。但屡战屡败,还是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郭光灿投身科研时就“无门无派”,此时更没导师指路、没师兄弟开解。在那些品尝孤独的夜晚,他常在夜深人静时戴上耳机听着那首《孤独的牧羊人》的歌。“一个人在苍茫的大地飘来飘去/一个人在无尽的祈愿里承受风雨/……等阳光融化了冰霜/融化了寒冬就温暖了牧场……”
难得的是,郭光灿回望所有这些经历,即便是三次折戟“973”,即便自己的研究被说成“伪科学”,也从没觉得委屈。“那时候得不到理解、得不到支持很正常——人们对量子信息太过陌生。”
对此,他的学生、中国科大物理学院教授张永生告诉《中国科学报》:“很多人说郭老师当年一直在‘赌’,其实不是,他从来没有‘赌’,而是一直相信,相信量子科学、相信国家。”在他心中,郭光灿是一个“遇到困难比别人更坚持一些,遇到事情比别人更乐观一些”的人。
6 给钱学森和路甬祥写信
连续申报“973”项目不中,郭光灿想,得把量子信息学研究的火再烧旺一些,让更多人理解。他变得愈加主动:在科普杂志开设“量子信息讲座”专栏、给期刊投稿综述文章、抓住机会开讲座作报告。
机会总是垂青于有准备的人。很快,属于郭光灿的机遇来了,而且一来就是两个。
第一个是,1998年,郭光灿有机会牵头组织一次有关量子信息科学的香山科学会议。
1993年由中国科学院和科技部共同发起创办的香山科学会议是很重要的学术交流平台。筹办之初,有人提醒郭光灿,会议要有影响力,得找一位大人物“镇场子”。
郭光灿不认识什么大人物。思来想去,“病急乱投医”的他,给大名鼎鼎的钱学森写信,请他担任会议主席。
“也没想钱老能不能收到信、看后是什么反应,当时就想找全国最牛的人物。”郭光灿后来对记者说。
没想到,钱学森不仅读了来信,还很快给郭光灿回复:“我很同意您说的我国应统一组织全国力量攻克量子信息系统的技术问题……但我现在已行动不便,已不能参加任何会议了。”
是年,钱老已离不开轮椅,郭光灿当然也是后知后觉。不过,能收到回信已让他喜出望外。
后来,他又去找两院院士王大珩。王大珩专于经典光学,但他触类旁通,马上意识到量子信息研究的意义,欣然同意参会。他说:“我们中国人必须在新的领域有自己的声音。”
这话正落在郭光灿心窝里,他眼眶一热。
郭光灿等到的第二个机会,最初只是个“小道消息”。
这个“小道消息”说:1997年,华裔物理学家朱棣文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作为嘉宾参加颁奖典礼。朱棣文在发言中提到,自己的相关成果能用于研制量子计算机。路甬祥听后记在了心里,回国后打听:国内有谁在研究量子计算机?有人说:郭光灿。
机不可失。郭光灿听说后当即给路甬祥写信,说明研究量子计算机的重要性,提到了他发表在PRL上的两个有一定国际影响的工作,最后开始“哭穷”,“希望中国科学院给我一些支持”。
这封信引起了路甬祥的重视,他把这封信转给时任中国科学院高技术研究与发展局局长桂文庄。
桂文庄是个雷厉风行的人。他当晚就带人来到合肥,刚住下就给郭光灿打电话:“我是桂文庄,中国科学院的。你能不能来一下?”
当时郭光灿正在香港讲学,接完电话,立刻买票返程。
听了郭光灿详细的介绍,桂文庄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极具生命力的新兴领域,并在回京后作了汇报。
没过多久,郭光灿真就“揭不开锅”了:他的两个基金项目都到期结题,按照当时的规则,要停一年才能申请新的基金。
他给桂文庄写信“求援”。桂文庄跟他推心置腹:“我现在最大的‘权力’,只能给你5万元的资助。”后来郭光灿才知道,这是极少以局长基金名义支出的一笔经费。
5万元也好啊,雪中送炭能解燃眉之急。但他“得寸进尺”:“可不可以再给我们立个项目?”
桂文庄考虑得更周全:“立个项目,做完就完了。”他建议郭光灿建立一个实验室,这样能有望得到长期的支持。
于是,1998年12月,郭光灿再一次给路甬祥写信,就“开展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研究”作了汇报。在中国科学院的一系列支持下,郭光灿在中国科大筹建了量子信息实验室,现为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重点实验室。
1999年,桂文庄向中国科学院党组举荐,破格让郭光灿的校级实验室参加院重点实验室的评估考核——好的评估结果意味着能得到更多经费。
谁都没想到,量子信息实验室居然获评信息领域第一名。这意味着,接下来的3年,实验室每年都能得到350万元的经费支持。私下里,郭光灿握住桂文庄的手说:“桂局长,我没给你丢人。”
7 燃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势
“973”项目的申报也传来好消息。
2000年,郭光灿第四次申请,拿到了中国量子信息领域第一个“973”项目。这一年,郭光灿58岁,已经在量子研究的冷板凳上坐了18年。
当时的评审组组长是我国著名的理论物理和粒子物理学家周光召,他对郭光灿的答辩内容十分认可。这次答辩,评委对量子信息项目一致通过。
在历次申请“973”项目的过程中,郭光灿都是“一个人在战斗”。他痛感这个领域太需要开拓。
“973”项目有2500万元。拿到“巨款”后,郭光灿没去想怎么把自己的“地盘”做大,而是想着“要在国内把整个领域带起来”。
该资助谁?郭光灿考虑,一要确保量子信息学布局合理,二要确保各个重要方向后继有人。基于这两条原则,他把国内“想做的、有可能做的”主要团队都聚拢起来。
1个“973”项目,8个课题,十几家单位,50多位研究人员,包含中国科大、清华、北大,中国科学院的物理所、半导体所、上海光学精密所、武汉物数所……已有的、正筹建的,他全都拉进了队伍。
5年后项目结题,成绩斐然。该项目不仅冒出一批研究成果,更在国内建立了若干量子信息科研阵地,尤其是培养了一批具有开拓创新能力的科研队伍。该项目中的若干名课题组长和项目骨干后来都成为院士,其后成为“973”项目首席的也有十几人。
这是中国量子信息实现由“从0到1”向“1到100”发展的一个转折点。郭光灿说,现如今中国能够在量子信息领域处于第一梯队,跟国家在2001年就开始从国家层面予以支持密不可分。
“有钱”之后,郭光灿逐渐将重点放在培养学生上。很多人说他眼光很毒,“发掘一个培养一个,培养一个成一个”。不仅有成为院士的段路明,还有韩正甫、郑仕标、郭国平、周正威、张永生、史保森、李科、周宗权、孙方稳、黄运锋、董春华……很多能够独当一面的后起之秀,在成长中都得到了郭光灿不计回报的支持。
他苦过自己,也苦过家人,但他敢拍着胸脯说,自己从没苦过团队里的年轻人。
郭光灿带研究团队还有个不成文的规定:组内学生经他指导发表的论文,可以写上他的名字,以让外人知道这项研究来自哪个团队,但他从不署名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20多年来,他一直坚持如此行事。
“郭老师团队的人不会被轻易挖走,因为郭老师给学生创造了最适合他们发展的环境。”学术秘书段开敏说。
郭光灿也有自己的小九九:想快速地把本土的青年科研人才培养起来。他对《中国科学报》说,看到量子信息科研在国内蓬勃发展、许多年轻人在不同的方向冲锋陷阵,特别有成就感。
“这是我80岁以后,一想到就会很开心的事。我有幸抓住了这样一个新兴学科,让它在中国后继有人,我完成了历史使命。”郭光灿半开玩笑地对记者说,“我现在已经是老头子了,可以‘在丛中笑’了,对不对?”
《中国科学报》 (2023-12-07 第4版 风范)